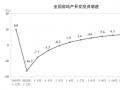《刺杀小说家》当技术和视效想要思考
2021-02-26 14:38:40 来源: 新华网 评论:0 点击: 收藏
时至今日,有关影片《刺杀小说家》,不少观众和评论者倾向于讨论其醒目的数字视效之于全片主题、叙事功能及其表达的意义,这确实是影片本身就想传达的主要信息,也是包括导演路阳在内的主创团队,从一开始就花费大量投入和不少心力执着探索的重要领域。尽管在不同的场合,路阳始终都在强调影片的创作跟当下观众的强劲关联,并希望观众明白,这部“很厉害”的电影,同样具备人物、故事与思想、情感,而不是只有重工业、大体量以及奇幻的视觉效果;但不得不说,这部在国内第一次完整使用虚拟拍摄技术,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化以及视效技术最新水平的影片,如果不对其技术探索和视觉效果予以评判,也就无法有效地评判其自身了。
当技术和视效想要表达和思考,电影就开始摆脱其原始的魔力及其奇观性带给观众的沉迷,从社会学和通俗文化的视野进入美学和独立精神的范畴。然而,这种试图以“特技”传达某种独特的哲理或诗性的做法,或以“视效”创建整体性的象征或隐喻体系的行为,往往就会僭越一般人群的认知水准,挑战普通观众的理解能力,并因票房失败而为项目本身带来不小的投资风险。遗憾的是,电影的历史及当前的状况,已经并仍在表明这一点。
但在大多数时候,好莱坞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可“正确”的好莱坞又总是遭遇电影内外与世界各地的各种解构和指责。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影评家波琳·凯尔(Pauline Kael,1919-2001)就严厉批评好莱坞生产的那些不断扩大规模、增强特效的大片,只为符合市场的逻辑而非攻克美学的难题,从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思想、个性以及激情和想象力。这种来自学界和业界的深刻批评,几乎跟好莱坞的技术拓展及其获得的全球霸权如影随形。受到好莱坞强烈刺激和深刻影响的中国当代商业大片,更是因资本的狂欢、特效的泛滥与内容的空洞、情感的冷漠,虽然吸引了观众赢得了票房,但却患上了波琳·凯尔早就描述过的某种“精神分裂症”。
诚然,即便在好莱坞,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迄今,电影也总在思想之中;电影的技术和视效同样如此。尤其如何通过电影思考技术和视效,或者说,如何通过技术和视效思考电影,也一直是包括《异形》《黑客帝国》《哈利·波特》《蝙蝠侠》《奇异博士》与《复仇者联盟》等系列电影暨视效大片有意无意都会指向的问题;或者说,往往成为部分观众、电影批评家或哲学家愈益关注并重点阐发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电影及其内蕴的技术和视效,已经成为当代哲学思考存在、时间与空间以及真实、虚构与信仰等关键概念的重要基点。或许,正是因为思想者或哲学家的参与,好莱坞的系列电影暨视效大片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票房回报和再生能力,而且彻底洗去了附加于其上的,关于其罪恶、肤浅或无聊的各种诅咒。当思想者们在《钢铁侠》中面对“史塔克现实”,宣称永远无法打败,都会重新站起来阅读漫画、观看电影和思考哲学的时候,史塔克胜利了,现实也胜利了。也就是说,电影胜利了,哲学也胜利了。
这种多方共赢的局面,跟中国电影和中国哲学无关。中国生产的不少系列电影暨视效大片,虽然也在忙于创造系列、建构宇宙,但世界观的幼稚或价值观的敷衍,以及急功近利带来的技术破绽或视效缺陷,特别是在叙事与情感等方面多年存在的痼疾,不仅很难令人真心认同其虚构的“人物”和“现实”,而且完全无法将其跟中国电影的“技术”和“哲学”联系在一起。
好在郭帆和《流浪地球》出现了,路阳和《刺杀小说家》也出现了。对于笔者而言,随着这两部大片的出现,中国电影的技术和视效也要开始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思考虚拟现实及其哲学命题了。仅就《刺杀小说家》来说,便试图跨越媒介、叙事与审美边界,整合作者、文本与类型功能,见证技术、艺术与工业水准并引领行业、产业与工业方向,其创意与创新堪比此前的《流浪地球》。
更重要的是,除了令人赞佩的技术创新、工业探索和视觉效果之外,影片在动作、思想与情感、趣味之间的关系处理,也达自然浑融之境。作为一部具有作者意味的商业片或商业诉求的作者电影,影片在整体象征、细节隐喻及其复杂意义的呈现方面,也表现出独树一帜的宏大格局。“小说家”的出场、石头的投掷姿势、钢笔在纸本上的书写、图书馆与文物字画的遭劫,以至日本动漫的深刻影响等等充满“怀旧”的各种因素,不仅为“技术”找到了相互对应的落点,而且为“视效”安放了思想甚或哲学的基底。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影片并未获得预想的票房业绩,但从超越票房决定论的角度,仍然可以高度评价这部影片的价值和意义。
技术不是“无思”,也不是“思想的障碍”;正如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2020)所言,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寻求生命。作为一种话语隐喻,当《刺杀小说家》里两个世界的生命以特异的方式互动共生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电影从思想甚或哲学的层面思考技术和视效的时候。
当技术和视效想要思考,我们便可以期待一个新的属于中国电影的时代来临。(李道新)